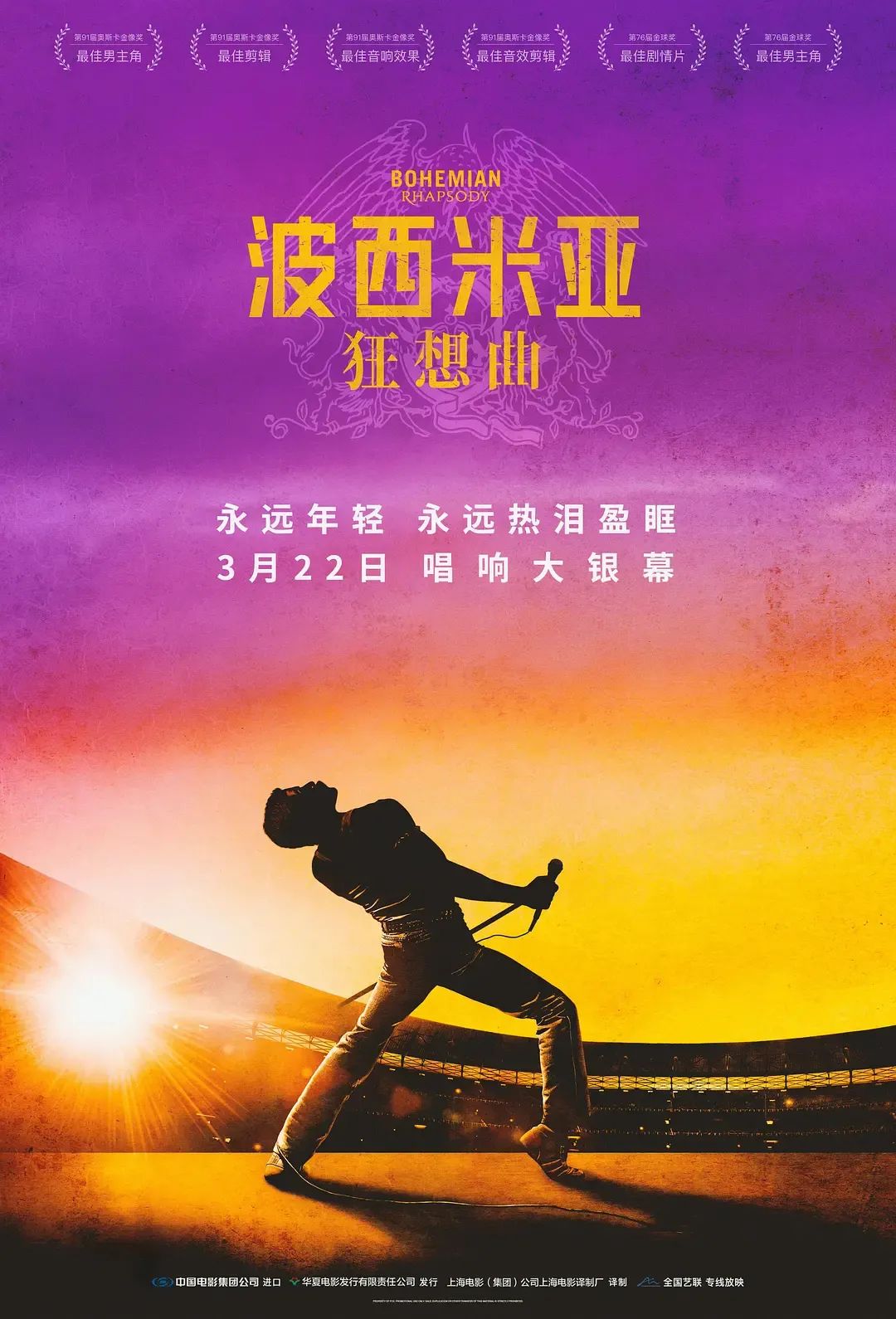《波西米亚狂想曲》:一场视觉怀旧盛宴中的叙事矛盾消解 日期:2020年11月04日
作为第一部描写皇后乐队及其主唱弗莱迪·摩克瑞(Freddie Mercury)的传记片,《波西米亚狂想曲》自2018年10月上映以来取得了巨大的票房成功,仅凭借约5000万美元的制作预算便在全球获得了8.69亿美元的票房收入,成为了2018年全球票房第六高的电影,创下了传记片和剧情片的票房纪录。
「一」 除了对皇后乐队1970、80年代诸多经典金曲的重新演绎,影片最让人震撼之处便是在最后20分钟完美还原了1985年7月13日盛况空前的“LIVE AID”(拯救生命)演唱会。这场由鲍勃·吉尔道夫(Bob Geldof)和米兹·尤瑞(Midge Ure)发起,旨在为当时埃塞尔比亚饥荒募集善款的电视直播义演堪称摇滚乐史上最著名的一次演唱会,不仅演出会场横跨英国伦敦和美国费城两地,还吸引了全世界100多位重量级的摇滚乐歌星参加:皇后乐队、鲍勃·迪伦、艾尔顿·约翰、保罗·麦肯特尼、蒂娜·特纳、大卫·鲍伊、麦当娜、U2…… 为了让观众获得身临其境体验这场伟大演出的沉浸感,影片《波西米亚狂想曲》从演员表演、服装舞美、灯光、道具、音响效果乃至多制式放映等不同方面均做足了功夫。饰演弗莱迪·摩克瑞的拉米·马雷克(Rami Said Malek)为了逼真还原弗莱迪极具感染力和戏剧性的舞台表演,在戏外对人物原型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并最终凭借对这一角色的出色演绎成为新晋奥斯卡影帝。曾七次获得奥斯卡提名的影片重录混音师保罗·梅西(Paul Massey)则从档案中查找到大量皇后乐队唱片的原声,以使影片能够达到定制体验的真实感。
学习艺术设计出身的弗莱迪·摩克瑞非常注重自己的舞台形象,他曾说:“你看到的不是一场音乐会,而是一场时装秀。”为了真实还原当时的每一处场景和舞台细节,服装设计师朱利安·戴(Julian Day)不仅参考了纽约著名迪斯科舞厅54俱乐部(Studio 54)的影像资料来设计人物造型,还直接找来当年曾为皇后乐队设计服装和皮具的设计师桑德拉·罗德斯(Zandra Rhodes)、罗伯特·奥尔索普(Robert Alsop)等人来为影片重新制作舞台演出服装。牛仔裤品牌Wrangler、运动品牌Adidas更是被邀请重新生产了弗莱迪·摩克瑞在LIVE AID演唱会上所穿的紧身水洗牛仔裤和拳击球鞋。 更为夸张的是,由简·塞维尔(Jan Sewell)所带领的妆发团队用四天时间在英格兰北部的旧货商场为影片的群众演员寻找符合80年代风格的服装,并设计了七千顶Mullet头假发以让这场“LIVE AID”演唱会看起来更为真实。各制作部门的精益求精使得影片成功打造了一场视觉怀旧盛宴,以至于斯蒂芬妮·扎克莱克(Stephanie Zacharek)在《时代》(Time)杂志上专门撰文称这是“一部感官主义者的电影”。
「二」 著名评论家卢卡奇曾在《叙事与描写》中主张要“选择一个可以在其命运中交错种种矛盾的人做主人公。”作为皇后乐队的重要核心人物,弗莱迪·摩克瑞堪称是一位绝佳的传记片主人公人选。他出生在桑给巴尔(Zanzibar),父母均为印度帕西(Parsee)人,17岁为了躲避战乱随家人移民英国。
1970年4月,他加入了皇后乐队的前身——由布莱恩·梅(Brian May)和罗杰·泰勒(Roger Taylor)组建的Smile乐团,他的音乐创作和演唱充满了激情,舞台表演风格又极具戏剧性和感染力,并因其超凡魅力和独特之处而持续不断地被票选为流行音乐史上最伟大的歌手之一。 然而音乐事业的巨大成功背后却是弗莱迪·摩克瑞对个人身份认同的困惑,他曾合法申请将自己的原名法鲁克·布勒萨拉(Farrokh Bulsara)更改为弗莱迪·摩克瑞,也因为私生活问题而屡遭媒体抨击。 这种内心深层的自我矛盾性在弗莱迪·摩克瑞创作的音乐中也可以一窥端倪,一方面他率真又嫉恶如仇,在Death on two legs中大胆地直接表达对经纪人的愤怒之情;一方面他的内心充满了对爱的渴望,Somebody To Love、Love of my life、Crazy little thing called love堪称最美的情歌;一方面他充满自信、积极热血,Keep Yourself Alive、We Are the Champions、We will rock you是皇后乐队最为人熟知的经典单曲。然而在弗莱迪·摩克瑞音乐世界的另一个角落,还藏着一个幻想中由国王Rhye统治的国度。而只有进入这个存在于Seven Seas of Rhye、My Fairy King、Lily of the Valley等乐曲中的神秘国度或许才能触碰到真实的弗莱迪·摩克瑞。
在I want to break free中包含了他对一切禁锢枷锁的反抗以及对自由的向往,在皇后乐队的成名曲《波西米亚狂想曲》(Bohemian Rhapsody)中他嘶喊着“有时我宁愿从未降生”(I sometimes wish I’d never been born at all.)……而这些词句或许才是破译弗莱迪·摩克瑞内心世界的关键密码。 影片《波西米亚狂想曲》的编剧彼得·摩根(Peter Morgan)也并没有打算回避这一点,在影片的两条主要情节线以及多处出现的对比蒙太奇剪辑段落中,一边是经典好莱坞剧作中行动的主人公弗莱迪·摩克瑞,他挑战种种困境并最终以凯旋告终:毛遂自荐加入Smile乐团、敦促乐队录制第一张专辑并获得著名经纪人约翰·里德(John Reid)的注意、创造性地将歌剧元素融入硬摇滚的作曲,创作出了在歌曲结构及时间长度都打破了当时流行音乐常规的《波西米亚狂想曲》,并为了力主将这首“进步摇滚时代最具创新性的作品之一”的乐曲确定为专辑《A Night at the Opera》(1975年)的主打单曲而不惜与唱片公司高管雷•福斯特(Ray Foster)闹翻。最终《波西米亚狂想曲》在英国音乐排行榜连续九周取得冠军,创下当时英国最高的单曲销售记录,从而确立了皇后乐队的地位。
而另一边则是在乐队的世界各地巡演中,弗莱迪开始质疑自己的个人身份,并因擅自更改名字和护照信息而与父亲发生冲突的情节线。弗莱迪在疯狂派对之后的落寞与孤独以及夜店中的迷茫眼神使得影片已经开始尝试触及到这位复杂主人公内心的多重维度。 然而此后编导对于情节的常规化处理却将复杂人物和尖锐的叙事矛盾简化、压缩至单一维度,为了达到最终的剧作目的,甚至不惜对真实的人物史实进行改写。而这部电影对矛盾的自我消解实际上也成为了其最值得分析和探究之处。
列维·斯特劳斯在《结构人类学》中认为:“神话的思维总是由意识到各种对立面的存在到寻找解决这些对立面的方法而层层递进、逐渐展开的……神话的目的就是要提供一个能够解决矛盾的逻辑模式。”因此在电影文本中找出相对应的二元对立组合机制就能够揭示出电影的深层结构。 在《波西米亚狂想曲》中,主情节线的叙事对立面被设计为反面人物保罗·普拉特(Paul Prenter)的谎言及其对弗莱迪的操纵行为,他不仅怂恿约翰·里德向弗莱迪提议应该追求个人事业离开皇后乐队,还百般阻扰弗莱迪与其他人的直接沟通。离开了团队的弗莱迪虽然获得了一份与CBS唱片公司签订的高达400万美元酬金的单飞协议,但是却也在德国慕尼黑沉迷于透支生命的生活方式,并感染了艾滋病。最终在玛丽的劝说下,弗莱迪开始意识到自己腐烂、堕落的生活,坚决解雇了保罗并“与母舰重新联系”。在获得大家的谅解后,皇后乐队在最后一刻获得了参加Live Aid演唱会的机会。 在全片的最后高潮时刻Live Aid演唱会开始前,弗莱迪携吉姆·赫顿回家探望了父母,两位老人最终理解了弗莱迪的感情生活,弗莱迪也因即将要去参加募捐演唱会认同了父亲一直以来的观念“Good thoughts, good words, good deeds”(睿智、善语、良行),父子二人得以冰释前嫌。
外部冲突和自我矛盾的两条叙事线在Live Aid演唱会上最终汇聚,走向了弗莱迪·摩克瑞一生中的高光时刻。这段20分钟的逼真视觉怀旧盛宴与当时真实录像版本的唯一不同之处便是编导不断地穿插弗莱迪的父母、乐队成员、爱人在电视机前、舞台上及后台为弗莱迪感到骄傲的微笑镜头,而这也实际是全片所要表达的主题“我们是一家人”(We are a family)的又一例证。 因为在影片中,任何会拆散皇后乐队的力量都会被编导所否定,保罗·普拉特被比喻为“肮脏的果蝇”,弗莱迪单飞时期与迈克尔·杰克逊的合作、首张个人专辑以及与西班牙女高音蒙茨克拉特·卡芭叶(Montserrat Caballé)合作的《巴塞罗那》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被影片彻底略写……对一部影片情节结构的整饬和结局处理反映的是编导的价值判断,而《波西米亚狂想曲》对于复杂人性开掘的浅尝辄止与普世价值观在影片中的绝对控制权更有其深层的社会原因。
「三」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曾将影像文本的书写视为“社会象征行为”,即其中隐藏着深层的乌托邦欲望,作为大众文化的电影通过对叙事结构的想象性解决来压抑社会的政治焦虑。在《波西米亚狂想曲》中,在皇后乐队的故事外壳下的乌托邦冲动便是对20世纪70、80年代那个已经消逝的理想主义大师辈出的时代的强烈向往。
从空中俯冲至万人涌动的伦敦温布利体育场的震撼长镜头,到演唱会现场钢琴上摆放精准的百事可乐杯子,再到拉米·马雷克对弗莱迪·摩克瑞演出当日一举一动的逼真模仿,这场精心设计的充斥着各种视觉历史符号的“摹拟体”(Simulacrum)有意将当下美国社会的一切文化特征进行隔离,通过沉溺于特定过去的泛滥影像进行特殊的历史与政治想象。 尤其是当今特朗普政府推行的移民政策改革造成的美国社会分裂以及民众的不信任感,亟需通过这场视觉怀旧盛宴中的自我矛盾消解进行精神投射。因此,在这部电影中,皇后乐队和弗莱迪·摩克瑞的真实历史被改写,皇后乐队的团结、在电视机旁被感动的泪流满面的母亲面部特写、玛丽·奥斯汀与吉姆·赫顿在后台的相视而笑、“我们是一家人”(We are a family)在Live Aid演出现场的精神呈现才是编导的真正意图所在。
至于真实的弗莱迪·摩克瑞,他其实在《大伪装者》(The Great Pretender)的MV中曾进行过真实的自我剖析:“I’m the great pretender”(我是个大伪装者)。在这支音乐录影带中,有一个无数个“弗莱迪·摩克瑞”在舞台上的象征性镜头,或许只有通过《公民凯恩》的多重限制视点、《基伯龙三日》的时间切片、《三岛由纪夫传》中现实、回忆与想象交叉的多重实验性美学结构等艺术手法我们才能真正触及到弗莱迪·摩克瑞的灵魂深处,并在历史真相和艺术想象中建构出真正的多层次生命写作。
虽然《波西米亚狂想曲》无意于去建立一个观察人性复杂性的认知视角,仅是通过延续经典好莱坞传记片的叙事传统再次确立了主流价值观所认同的公共历史。然而无论是作为一部重返充满理想主义光辉的1980年代的怀旧乐迷手册,通过ScreenX放映格式获得摇滚乐史上最著名的“LIVE AID”演唱会的震撼体验,还是作为一个考察当代美国社会的文化研究样本,相信你都会能在这部描写皇后乐队和弗莱迪·摩克瑞的传记影片中有所发现。
作者:徐立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