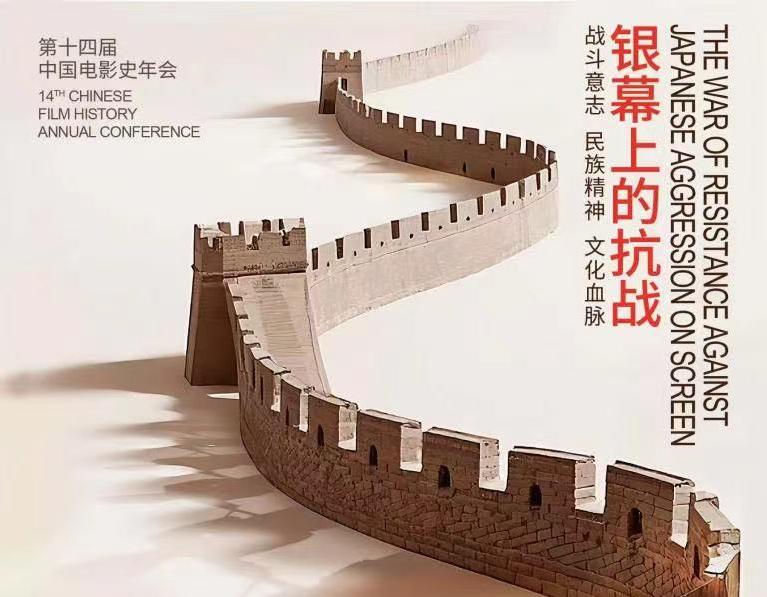第十四届中国电影史年会
主论坛发言

钟大丰(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 教授)
题目:《从寻找北洋秋操影像说起:谈谈数字时代电影史研究中的影像分析》
栗琳《一九〇五年清政府拍摄电影 <秋操> 考》一文通过对于1905年10月北洋新军秋操期间曾经进行活动影像拍摄进行考证,提供了目前最早直接可靠的有关国人进行电影拍摄的记载。然而,该文对于影片本身和相关影像的存留与传承情况未做论及。为此寻找秋操影像成为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关键任务。遗憾的是,虽几经找寻并找到了一些疑似片段,但在对军装、军衔、装备、旗帜、操典等影像细节进行辨认后也大致可以排除其为1905年《秋操》,只能说有几段有较大可能是1906年“彰德秋操”的影像。即使这一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但也仍是一次很重要的尝试,AI技术的兴起很可能为这一工作的继续开展提供便利。当下,AI技术在完成大规模、快速处理信息的重复性劳动方面表现出巨大优势,但只有通过“AI指令系统构建能力”和“人机协作项目管理”使人类的创造性工作与之结合,才能真正为影像分析提供新的可能性,助力侧重解构的“媒介考古学”和侧重建构的“影像史学”取得新进展。

虞吉(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 教授)
题目:《抗战大后方电影“特殊历史作用”再审视》
抗战大后方电影的特殊历史作用是近三十年研究持续关注的核心聚焦。自1998年第七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特设的“重庆与中国抗战电影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重庆与中国抗战电影学术论文集》以来,对抗战大后方电影“特殊历史作用”经历了从浅表、局部到深入的揭示与阐释的三个阶段:首先是直观历史现象概括与归纳的“桥梁论”;其次是注目纪录片史的“补足效应”与“纪实性革命”;最后是中国影剧现实主义的体系化与在地化完成。这一学术认知上的演进,不仅重塑了抗战大后方电影的史述外观,一定程度上也赋予了抗战大后方电影新的历史评价的权重;大后方电影,作为抗战时期中国电影具有主流与主导地位的区域电影,其之于整个中国电影历史发展的历史动力学机制,便得以层层彰显。

聂欣如(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教授)
题目:《纪录片 <民族万岁> 研究补正》
郑君里在1943年抗日战争时期制作的《民族万岁》是那个时代重要的纪录片之一,对这部影片的研究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意见。首先,关于类型归属问题,以往的研究大致上有三种不同的说法:民族志(人类学)纪录片、诗性纪录片和政治宣传纪录片;由于郑君里所属的国民政府政治部三厅的主要职责便是抗敌宣传,因此将《民族万岁》归类于政治宣传纪录片应该是准确的,且并不含有贬义,是彼时的实际社会需求使然。其次,关于纪实与戏剧性的问题,《民族万岁》因有大量搬演的片段而被质疑是否属于纪录片,但是搬演也确实是纪录片在某一个历史时段中所难以规避的特征;而影片中呈现的诗性也不应当成为其被否认为纪录片的理由。最后,关于民族志的问题,将《民族万岁》说成是民族志纪录片的提法首先要区分概念的狭义与广义,然后才有可能进行有价值的讨论;将《民族万岁》与弗拉哈迪影片相提并论,需要在美学上区分表演的虚构与非虚构。

晏妮(日本电影大学 特任教授)
题目:《孤岛和沦陷时期的中日电影相关历史——韬晦的文本与非协力的抵抗》
1939年成立的“中华电影公司”由川喜多长政主导,其进入上海影业交涉时甚至持枪胁迫,折射权力不对等的紧张态势。这一时期,中国影人的创作策略被迫转型:孤岛时期借古装片借古讽今,沦陷后遭禁,只能拍摄时装言情片。朱石麟坦言“我们只能在刺刀下拍爱情片”。但值得注意的是,中联/华影时期并无一部真正所谓“协力日本”的影片,影人通过题材选择实现了消极抵抗。同一文本如《木兰从军》的接受差异凸显地域政治:孤岛上海视为抗日隐喻。“话剧抗日、电影附逆”的二分法不成立。话剧依赖语言壁垒形成抵抗空间,而电影面临更严酷的审查。研究需关注影人思想流动性及非对称权力结构:在日方绝对控制下,中国影人通过“韬晦”的创作践行了一种“非协力”的抵抗。理解这段历史需剖析机构管控、创作策略与受众解读的复杂性。

范倍(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 教授)
题目:《 <新蜀报> 副刊中的电影资讯:大后方电影文化境况考察》
《新蜀报》副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通往历史的通道,让我们能在历史的尘埃中发现被掩埋已久的史实,加深了我们对大后方电影史的了解。自1937到1945年,《新蜀报》电影副刊共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37年创办的《文化与生活》;第二阶段是1938年的《新光》、《新副》以及《新光戏剧周刊》,以及1939年到1943年8月的《文锋》、《七天文艺》以及这5年间散落在《新蜀报》各版的电影内容;第三阶段是1943年8月到1945年8月的《影与剧》、新《影与剧》以及《电影》副刊。《新蜀报》副刊的内容主要包括域外电影状貌及经验介绍、宣传文章、知识普及与理论批评。除此之外,《新蜀报》电影副刊最重要的是将抗战期间陪都电影业的发展按照时间顺序囊括其中,尤其是对中国电影制片厂以及中央电影摄影场的报道介绍提供了大后方电影史的第一手史料,对我们补充中国电影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徐蓓(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 教授)
题目:《激活沉寂的档案:历史影像在纪录片中的叙事力量——以〈大后方〉创作为例》
《大后方》的创作始于对历史影像力量的探索。2013年项目启动时,《大后方》团队在史料匮乏下,自行收集资料建立影像资料库。历时一年,团队足迹遍及中国十余省市、港澳台、日本和美国,最终积累了大量珍贵影像。2014年10月我们正式启动创作,首先希望营造可感知的历史记忆。开篇摒弃“西安事变”的常规叙述,选用1930年代四川都江堰民众生活片段《中华儿女》,使“大后方”具体为土地与人民的鲜活存在。其次,影像能揭示被遮蔽的历史细节。比如几乎没有现代医疗条件下,林可胜博士在贵州建立红十字中心,团队通过在美国纪录片《苦干》中发现林博士影像,首次公开其贡献。更重要的是,影像的蒙太奇叙事可重构历史逻辑,例如,将日本士兵机械装填炮弹与中国阵亡士兵的画面拼接,能形成深刻的情感冲击。我们不是影像的生产者,只是搬运工。在此,向所有留下珍贵影像的前辈和与我并肩作战的团队致以最深敬意。

李镇(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研究员)
题目:《烽火传檄——1940年“西北摄影队”远征之观察》
1940年1月至10月,西北摄影队的万里远征是中国电影史上一次兼具地理跨越与政治象征意义的特殊行动。这支由43名多领域专家组成的队伍,以拍摄《塞上风云》外景为名,穿越重庆、延安、榆林、绥蒙等多元政治空间,在288天的征程中完成了影像生产、抗战宣传与文化拓荒的三重使命。其行动轨迹勾勒出战时中国的政治地理图谱,通过电影这一现代媒介在边疆与内地、传统与现代、国共两党之间架起了文化认同的桥梁。在榆林,邓宝珊部动员五千人欢迎,彰显统战价值;在绥蒙,中共掌控的新三师全力协助拍摄,活佛阿克旺成为“抗战解说员”;两赴延安,摄影队受到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接见,毛泽东亲笔题词“抗战、团结、进步”,返渝后引发“延安热”,并催生1941年雾季公演。摄影队通过流动放映、文艺演出、社会调研、文化惠民、医疗援助,打破边疆信息封闭,用影像建构“蒙汉一家”的共同体想象。《塞上风云》成为抗战时期民族团结的重要影像,亦引发国共在文化领域的激烈博弈。此次远征开创“创作与田野调查结合”模式,不仅积累边疆文化工作经验,也为战后现实主义电影创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黄望莉(上海戏剧学院 教授)
题目:《抗敌演剧队“复员”影人研究》
抗战胜利后的“复员潮”是中国电影史上兼具政治战略与文化转型意义的人才流动。以抗敌演剧队为核心的两千余名文艺工作者,在1945至1947年间通过合法返沪、香港中转、木船运输三条路径完成撤退。周恩来统筹“相机撤退”策略,既规避了国民党阻挠,又保存了骨干力量。徐桑楚率剧宣五队借道香港分赴南洋,应云卫则秘密将“中艺”全员运回上海。这支历经皖南事变等政治挤压的队伍,积累了活报剧与纪实美学经验,为战后现实主义电影奠定基础。返沪后,郑君里、陶金等人创作了《一江春水向东流》,陶金等将战地剧目表演经验转化为“哭戏”等银幕语言。演剧队成员主导成立联华影艺社,后并入昆仑影业,与“中电”“中制”分庭抗礼。阳翰笙等发起《致政治协商会议意见书》,公开挑战国民党电影垄断。1948年昆仑影业推出的《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其群像叙事与市井写实风格,直接脱胎于演剧队在战地创作的活报剧形式,标志着左翼电影传统向“人民影像”美学的演进。抗敌演剧队的复员行动,本质上是文化力量在历史转折期的战略性转移。影人们通过空间迁徙完成身份转换,将战时积累的创作能量释放于银幕,既延续了左翼电影传统,又为“人民影像”美学的形成奠定基础。

吴国坤(香港浸会大学 教授)
题目:《 <香港1941> : 香港电影的抗战记忆》
香港电影对抗日战争的影像再现,始终与地域政治和身份认同交织。1930年代“国防电影”论战中,蔡楚生倡导的社会写实主义与侯曜的浪漫主义形成美学对峙,实则是国家话语与地方娱乐的博弈。抗战期间,香港特殊的政治环境使其成为检验“中国性”与“香港性”的文化实验室。战后南来影人创作的《花街》等作品,以庶民视角重构战争记忆,通过家庭伦理剧延续上海电影传统,既规避国共意识形态之争,又形成“感伤中华”的独特叙事。左派批评其逃避现实,却印证了香港作为超越政治藩篱的创作空间。1980年代《等待黎明》将1941年香港沦陷与“九七焦虑”并置,影片对殖民者的讽刺、日军暴行的揭露,以及周润发饰演的“江湖义士”叶剑飞,共同建构了非典型抵抗叙事。这种既非传统英雄亦非汉奸的形象,体现了香港在历史夹缝中的身份探索。从国防电影的政治宣教到《等待黎明》的个人化叙事,香港抗战影像始终是应对身份危机的文化实践。这些作品不仅记录历史,更在殖民与回归的变局中,为香港寻找自我定位的文化坐标。

安燕(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教授)
题目:《生活在艺术中采取自己的形式——中国战争电影中的“军民鱼水一家亲”》
“军民鱼水一家亲”通过弥散、无定形、不连贯力量的联合,呈现出一种运动变化的政治样态,最终形成整体化的团结形象,其“解放的幸福”场景与氛围,传递热烈、欢乐等情感,是生活在艺术中自我呈现的形式。从历史看,党的领导人以鱼水喻军民关系,作为革命战争根本原则,对文艺创作影响深远。中国战争电影创作里,抗战时期起,“军民团结”主题不断深化,在电影中演绎为政治理论与军事场景的美学表达,既关联历史现实,又不单纯是政治美学化,而是对历史理性与必然性的实践呈现。如诸多影片,借生活化场景,像《董存瑞》中情感与革命融合、《南征北战》里生活对政治场景的丰富等,展现军民鱼水情,让政治叙事有了生活温度,为历史进步叙事增添私人、感性色彩,开辟的政治—美学叙事策略与情感结构,值得深入探究,为理解中国战争电影及背后的政治、美学关联提供了关键视角。

秦翼(南京艺术学院戏剧与影视学院 教授)
题目:《作为中国电影的一次“存在”之证——沦陷时期电影 <红楼梦> 拍摄前后》
1944年“华影”时期,卜万苍改编执导了电影版《红楼梦》,该片拍摄呈现中国电影“存在”危机及影人“沉沦”抉择,是沦陷期上海电影人觉醒体现,为上海沦陷电影作中国电影存在之证。沦陷期上海电影人有“附逆”争议,但部分是留沪保国产电影,以“最小合作”存上海电影、阻文化侵略。电影《红楼梦》是影人面临精神灭亡危机的自救,影片借中式元素呈现民族文化积淀,以人物抉择表露内心坚守,为解读影人心态留途径。同时,沦陷期还有《渔家女》《还乡记》等众多影片,展现彼时社会现实、人物挣扎,150余部影片藏着沦陷时期创作者的内心剖白。在数据库与人工智能助力下,需深耕史料,填补历史缺口,完成有温度的历史分析,寻中国电影存在之证,也是电影历史书写的存在之证。
整理:赵敏、张释月、王成博